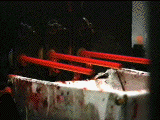.jpg)

热点排行
毛笔选择对书法创作的影响浅议2(连载)
人们对器材的关注与探索由来已久,关于器材的论述多散见于历代书论或著述中。从书论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诸多器材中,笔的作用无疑居于首位。在历代书论中,关于毛笔的记述由简单逐步趋于翔实,其中既有继承亦有变革。历来书家书论都十分重视毛笔的作用与品质。
康有为关于笔心及副毫的论述仍然为传统一路。在《广艺舟双楫》中,他认为书道犹如用兵,心意为将军,笔锋为先锋,副毫为士卒。选毫犹如选先锋,如果锋毫质量伪劣,做工不精,那么笔锋挥洒不能尽如人意,如此先锋就是必败的骄兵。如果锋受令而众副毫不齐心协力,则副毫就是游兵散勇。[11]
通过历代书论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毛笔对书法的意义和作用。下面再结合书家的创作来讨论书家择笔的问题。在创作中,毛笔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书家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笔来挥洒。在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中,纸犹如战阵,笔如刀和矛,墨如铠甲,砚如城池。可知,书法创作中毛笔的关键性。宋代米芾告诫:不称意的笔就如弯曲的筷子、腐朽的竹篙,使用起来费力不讨好。书家书写中碰到不称意的毛笔时,必欲换之而后快。这往往能在历史中找到许多生动的记载。为了适应新的书写载体,提高毛笔的性能,书家也经常参与制造或改良毛笔。张芝习书勤苦,家里的衣帛,必先用来书写而后煮练制衣。以篇幅宽大的衣帛习字,便于行笔疾速。可以推测其所用的帛,即使经过加工处理也比之简牍吸墨既快又多。故张芝改良毛笔的形制,以便连绵而书。张芝改良毛笔使用衣帛书写无疑加速了今草的形成进程。其主要原因在于绢帛面积大,可以多行并列书写。于是自然要求书家关注行与行之间的章法关系,从而影响到单字的结构与用笔问题。
书家大多对毛笔十分讲究。当创作遇到佳笔时,必然神采飞扬;而遇到劣笔时常常大发牢骚,怨气满纸。鲜于枢在所书《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抱怨毛笔质量低劣,以至换了三次笔才写完这首诗。其款文曰:“右少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玉成先生使书,三易笔竟此纸,海岳公有云,今世所传颠素草书狂怪怒张,无二王法度皆伪书。”[12]可见,好笔难求。原因何在呢?鲜于枢在其《赠笔工范君用册》中提出百工之技,唯制笔难得其人。并指出其原因在于制笔要通晓书法,而书法难通。此外,制笔的能手因为贪利而失败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好笔难求。
更为糟糕的情形发生在王宠书《王昌龄诗》的时候,他竟然换了八次毛笔,而原因不在于笔的质量。明代嘉靖五年,王宠应朋友之请书写王昌龄诗十二首。所用的纸为吴中新制的兰色粉笺纸,极为损笔,以致于八易其笔才写完此卷。王宠在《王昌龄诗》卷尾跋道:“年甫简持此卷索书,乃吴中新制粉纸,善毁笔,凡易八笔,方得终卷,中山之毫秃尽矣,勿怪余书不工也,当罪诸纸人,王宠识。时丙戌十月既望。”[13]由此亦见王宠对笔极为敏感,可谓精益求精。可想见纸笔不合给书家带来痛苦与无奈。由于频繁更换毛笔,此卷后半部分明显比前半字形大了许多,行气受到严重破坏。来源:《中国书画》
2011年0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