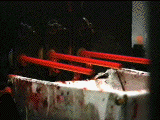.jpg)

热点排行
毛笔选择对书法创作的影响浅议3(连载)
人们对器材的关注与探索由来已久,关于器材的论述多散见于历代书论或著述中。从书论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诸多器材中,笔的作用无疑居于首位。在历代书论中,关于毛笔的记述由简单逐步趋于翔实,其中既有继承亦有变革。历来书家书论都十分重视毛笔的作用与品质。
有人认为为笔墨不佳,长期使用对书家或初学者都不利,久之易坏手法,后患无穷。元末曲阜人孔齐《至正直记》卷二:
“笔不好则坏手法,久而习定,则书法手势俱废,不如前日矣。……此吾亲受此患。
向者在家,有荆溪墨、钱塘笔,作字临帖,间有可取处。及避地鄞县,吴越阻隔,凡有以钱唐信物至,则逻者必夺之,更锻炼以狱,或有至死者。所以就本处买羊毫苘麻丝所造杂用笔,井市卖具胶墨,所以作字皆废。”[14]可见,孔齐以前用惯了荆溪墨、钱塘笔,后来到偏僻的鄞县只能使用羊毫苘麻丝所造的笔和低廉的墨。因此,他将书法水平的下降归咎于工具。事实上,历史似乎也不尽如此。史载颜真卿年少时因家贫以黄泥练字,同样,怀素年轻时用芭蕉叶及木板练字。此二位大家并未因黄泥与芭蕉而毁坏了他们的手法。
按常理而言,书家必择笔。然而,历史上也有不择笔而佳者,如欧阳询、虞世南等。陈槱《负暄野录》载,俗论云:善书不择笔,盖有所本。褚河南尝问虞永兴:“吾书孰与欧阳询?”虞曰:“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裴行俭亦曰:“褚遂良非精墨佳笔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余与虞世南耳。”但陈槱又补充道:“余谓工不利器而能善事者,理所不然,不择而佳,要非通论。”[15]可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乃为普遍规律,而不择笔也只是特殊现象。又如书家灵感涌现,激情四射,偶然欲书,不择纸笔也能创造出杰作来。所谓无意于佳乃佳,颜真卿用秃笔所书《祭侄稿》便是一例。“废纸败笔,随意挥洒,往往得心应手。一遇精纸佳笔,整襟然坐,公然作书,反不免思遏手蒙。所以然者,一则破空横行,孤行己意,不期工而自工也。一则刻意求工,局于成见,不期拙而自拙也。”[16]
笔墨精良固然能激发创作欲望,然而过犹不及,精纸佳笔也可能因主体过于在意而适得其反。废笔败笔,任性挥洒,不期望佳妙反而达到了佳境。这说明在艺术创作中,创作主体永远是决定因素,而作为客体的器材仅仅为辅助因素。
必须说明清楚的是,书家不择笔,并非不择优劣,而是不择新旧。佳笔即使用秃了,仍具有齐健圆的优点,照旧能得心应手。劣笔即使新的也不可能称心如意。所以王右军父子非宣城陈氏笔不书,韦诞喜用张芝笔,东坡喜用杭州陈奕笔,就是这个道理。
总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材料的选择不仅是创作的客观基础,对风格的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不管是清以前的硬毫与熟纸的搭配,还是清代羊毫与熟纸或生纸的结合,古人在材料的使用上不断变革尝试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来源:《中国书画》
2011年0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