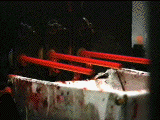.jpg)

热点排行
全球化的重构
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和今年COVID-19疫情导致的全球贸易冰封,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文世界讨论“全球化”的文章越来越多。我们最近大半年都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展开,而是选择在去年讨论的基础上继续观察,其间阅读了不少中文世界关于全球化的文章,直白的讲,其中大多数(很想说绝大多数,但好像有点伤人)都没有任何价值。原因很简单,中国在这一轮全球化过程中是主动选择“被全球化”的,只有极少数企业真正实现了全球化(也就是处在产业链的全球顶端位置),绝大部分企业仍然只是全球化产业链的一个环节。甚至那些目前在美国估值最高的中概股企业,都谈不上一个全球化的企业,一个企业的估值跟是否全球化也没有必然联系。
所以今天要我们许多金融届的明星分析师和身在书斋中的各位专家,一下子要从中国思维、A股思维转换到全球思维,这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毕竟他们是被动身处其中,而不是像欧美曾经那样,是不同时代全球化的设计者和建构者。
我们这两天重启“全球化”这个话题,是希望像去年一样,为困惑的当下,提供一点“不同的声音”。我们也相信,本文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在目前中文世界,是独树一帜,也是有足够份量的。
本文设定的阅读对象是广泛的,包括政府决策者、企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对这个话题有所关注的大多数人。本文可以看作是去年《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上)》和《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下)——美国的问题与中国的挑战》两篇的展开,尚未阅读前两篇的文章读者,为了更好的理解,建议先行阅读;老读者,可以先重温。
一、本轮全球化的关键问题
我们所说的这一轮全球化,不是一个特别久远的事,用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话来讲,就是GATT之后,从WTO起算的全球化。在欧美关于全球化的研究著述中,与globalization密切相关的是关于全球经济不平等的研究。所谓的全球经济不平等,是指在偏向自由放任主义的WTO框架下,由于资本全球自由流动,而税收和基于税收的社会保障网络无法全球统一,所导致的国与国之间以及一国内部(这个阶段尤其体现在发达国家内部)所形成的经济不平等局面。
中文世界目前关于全球化的许多论述,要么极其宏观的讨论长达千年的全球历史,或者回溯到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去讨论现代国家的形成,要么局限于细微的产业链影响,其实都已离题万里。我们也不好说那些不算研究成果,但那些研究对于理解今天这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对于为今天的决策提供帮助,为各界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确实没有太多用处。
本轮全球化的主导者是美国,偏向自由放任的WTO体系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这个体系导致了美国国内的严重经济问题,所以曾经的主导者要放弃。由于本轮全球化的主导者美国要放弃,而非主导者(包括欧洲、中国、日韩新等东亚诸国)均没有想放弃,才出现了一系列剧烈的反应,这是读者必须第一要牢记的。不要认为美国放弃WTO体系下的全球化,是中国某些舆论导致的,中国的舆论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当然反过来,自己的舆论是否会加速某种情况到来,从而使自己准备不足,也是值得反思的。
我希望读者记住的第二句话是,所谓“美国国内的严重经济问题”,就是美国国内的分配问题,也就是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问题。如果仅仅有差距,或者差距较大但中下层仍然生活较好,都不是问题。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严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先甜后苦、今不如昔,曾经被赞誉的橄榄形阶层分布,已经荡然无存。
美国目前的阶层分布不再是稳定的橄榄形,而是顶端有个不到5%的小三角,中上部是一个35%的梯形,而中下部是一个60%的大梯形,也就是从一个橄榄形社会重新回归了金字塔社会。而这个变化,只用了不到50年时间。关键在于,北欧、德国、法国,以及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并没有出现这个逆转。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是,那代经历过经济辉煌的美国中产阶级及其子女,现在大部分还是在世的。这种一生之中向下坠落的感觉所带来的心理冲击,使美国曾经的中产阶层,更易于把选票集中投给能够唤起他们辉煌记忆的人。
二是医疗、教育成为个体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
医疗、教育在大多数国家都是一个公共产品,都是通过公共体系去解决的。医疗是一个现代社会安全网的关键,而教育则代表了中下层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要深刻理解,一个社会的分配体系对个体而言,除了个体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益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从公共资源中获得的利益。公共资源的多寡,是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不同体制争论的焦点,这些争论的背后,是对不同政治经济理念的取舍。新自由主义偏向自由放任,这就把美国推向了拒绝财政主导的公共资源分配体系。在此前的文章中,我们把美国这个特殊的公共资源分配体系称为“信贷福利主义”。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以财政为主要公共资源分配体系不同,美国在公共福利这部分,拒绝税收下的财政主导,十分市场化。
新自由主义的口号是很动听的,也就是如果政府通过征税将民间财富聚集后再分配,将会不同程度的剥夺民众利益。所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选择是,把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的分配留给市场去解决。
今天大家都知道,美国医疗资源自由市场化的结果,是使美国个体背负了沉重的医疗负担。一个庞大的医疗保险市场和昂贵的医药、医护市场形成了。2019年度美国Fortune 500中,有40家医药巨头和20家保险巨头,而在1990年时,这两个数字分别为21和0。这个数字的背后,对应的是美国医生的高薪。根据Medscape Compensation Report 2019,美国医生平均工资收入达到了31.3万美元/年。分科来看,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Public Health & Preventive Medicines)医生的人均收入是最低的,为20.9万美元/年;骨科/矫形外科(Orthopedics)的人均收入最高,达到48.2万美元/年,接下来是整形、心脏病、皮肤病、放射、消化道和泌尿科的医生,他们的人均收入都超过了40万美元/年。在这样的人工成本下,再加上美国医疗系统对药物和医疗器械没有集中采购压价的制度,就导致美国的医疗价格十分昂贵。个人要把这种昂贵转嫁出去,就只能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显然,完全市场化的保险公司也不是善类。20家保险巨头带来的,是至今将近2,800万美国人无法购买任何保险的现实,以及大量中下阶层只能购买鸡肋一样低端医疗保险的现实。财政只能负担针对退休老年人和法定贫困群体的医疗保险。昨天美媒一则报道令人十分难过,一位美国新冠肺炎患者,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谁来买单?”尽管此前白宫已经宣布COVID-19检测和治疗费用不需要个人负担,但普通患者仍然非常担心这是否事实,这是怎样一种现实处境?
教育方面,美国教育的个人未清偿负债已总计超过1.6万亿美元。美国的大学教育体系为优秀的教职、研究人员提供了丰厚的薪酬和良好的待遇,财政不补贴教育的结果,是高昂的学费要由个体来承担。不负债、无大学,这对美国的中产阶层下一代而言,是无法逃避的现实。
三是将近40%的美国人,手停则口停。
按照美联储2019年的抽样统计,39%的美国人在需要应急支出400美元时会遇到困难,其中12%的人完全无法应付400美元的突发支出;而剩下27%的人,无法撑过一个信用卡周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会在疫情之后要紧急批准对民众的人均1,200美元拨款,这其实是帮他们撑过3个月时间。但这个数额是完全不够的。因为美联储的抽样统计是基于平时个体仍有收入时做出的,也就是每月收入还贷之后个体仍然可支配的存款或信用额度。而疫情期间,大量服务业从业者直接失去了收入,比如我们看到,奥兰多迪士尼乐园的4.3万名员工下周将开始放无薪假,这部分人既无收入,也不算失业,失业保险也无法领取,但个人的贷款还需要支出。这还是大企业的员工,对于非常多中小企业的从业人员而言,失业总数会非常庞大。美国劳工部目前的预测是,四月美国的失业人口将超过2,000万人。显然,美国的疫情也不可能很快结束。尽管我们也知道,疫情控制之后,相当部分人是会复工的,收入也会恢复,但美国普通民众背负的债务是十分现实的,最好的结果是顺延,而不可能减免。
所以为什么美国要放弃本轮全球化呢?因为它的内部贫富分化已经到了一个十分尖锐的时刻。医疗、教育、就业是三个核心议题,说到底都是民生问题。从选战来看,代表民意的要么是右翼民粹势力、要么是左翼民粹势力,为什么中间派没有任何机会?因为已经到了必须通过利益重新分割才能解决问题的阶段。
事实上,要解决美国国内目前的问题,逻辑上并不难,也即:
一是彻底改革医疗、教育体系,让这二者像欧洲或日本那样,以公共资源的方式去分配给个体。
二是拿回因全球化外包而丢失的大量就业机会,主要是制造业就业机会。
但现实却很困难。
一是因为彻底改革医疗、教育体系要动利益集团的奶酪,而代议制民主却面临代表谁的问题。如果以财政税收为依托去替代美式信贷福利体系,一方面要让美国民众接受增税(桑德斯和沃伦都主张的富人税),另一方面还要直接影响医药巨头、保险巨头和所有医护人员的收入。而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在这个时候起了负面作用。按照沃伦在其著作This Is Our Fight中的披露,美国"企业目前每年用于游说参众两院成员的经费,已超过纳税人用以维持参众两院的经费支出"。换言之,今天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在具有剧烈利益冲突的关键问题上,不可能去代表处于弱势的民众一方。政客们最有利于自身的做法,是在利益集团和选民之间周旋,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而川普政府,则是通过全民减税买来了选民现实的支持。但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应该是针对中下层定向减税,同时使整体税收增加,将医疗和教育归于公共资源加以分配。但增税这个问题,在目前的美国,是无法达成统一的,因为目前的美国主流民众,在过去几十年,已经接受了小政府、低税收、市场化公共服务的理念。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大多数年轻人是支持桑德斯的,这意味着,在未来10-20年内,美国的信贷福利体系将会从今天的剧烈动摇,到最终发生剧变。这种改变如果发生,将会实现美国内部利益的重新分配,极大的缓和贫富矛盾,同时为阶层变迁提供新的机会。这种内部利益重组,总体上将有利于美国,当然也有利于全球,但目前时机未到。
二是美国要增加长期就业仍然困难。除了上述公共资源的分配以外,就是个体收入的分配问题。美国能否再将制造业产业链拉回去,以恢复制造业的方式来解决就业,这个问题是充满争议的。今天国内对此的讨论也非常多,尤其是企业界。普遍的观点是,美国不太可能再把制造业岗位全部拉回去,甚至大部分拉回去都很难,理由是中国产业链的高效是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美国资本家也要赚钱。这是站在自己的视角看全球,不能说完全错,但这种思考是不周全的。我们从两个视角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从美国精英阶层的视角看
在美国,有部分精英人士其实已经默认了中下层未来的就业机会将会逐渐减少,所以“无条件基本收入”这个概念被反复提及。这个概念不是华裔总统候选人杨安泽最早提出的,在1960年代,美国一些地方就尝试过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制度,芬兰也做过类似的社会实验。Bill Gates等也提到过这个选项。这个制度之所以今天再被提起,是因为美国部分精英认为,随着机器生产时代的到来,大量人口将沦为无用阶层,实在没有办法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但问题在于,“无条件基本收入”仍然是要靠增加税收去解决,而在美国,又如何才能立法大幅增加税收呢?这就又回到了前一个死胡同,至少目前仍然是死胡同。
但从美国精英阶层的视角,长期看,如果预期未来要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决中下层的收入来源问题,那就意味着美国在人口数量处于少数的中上阶层将承受更多的负担,未雨绸缪的看,如何才能以少数人的智慧来养活多数人?只能靠继续保持经济上的优势。所谓经济上的优势,是指两方面,一是继续保持高科技优势带来的直接海外收入,二是继续保持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带来的铸币税优势去维持信贷福利。这两方面又有依赖关系,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说到底是以全球贸易无法离开这种货币为前提的,而全球贸易无法离开某种货币的最终理由,只能是发行这一货币的国家能够向其他国家提供关键不可替代的产品,一旦这个国家的关键产品是可被替代的,那么这个储备货币地位就可能顷刻瓦解。
那么今天美国能为全球提供的关键不可替代产品有哪些呢?农业是可替代的,石油虽然实现了出口国地位但也是可替代的,中低端制造业美国本土已经快没有了,服务业中的外贸部分(诸如旅游、影视)其实是可有可无的。说到底,只有产业链高端那部分既必需又无法替代。如果美国在产业链高端这部分失守,那么美国的地位将真正一落千丈,美元体系将面临瓦解。这就是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高度警觉的根本原因。维持美国科技绝对领先地位,才能维持美元体系,也才能未雨绸缪的为远期解决美国国内经济问题提供一个至关重要的选项。由此,我们应当能够充分理解,美国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遏制必然是长期的,而且将会有越来越极端的措施。在这方面,任何幻想都是不切实际的。牢牢记住,美国遏制中国高科技行业的发展,不仅是简单的国与国较量,或者本届美国政府的选择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由美国自身面临这个历史阶段无法克服的困境所决定的。
要理解美国,不能只看精英阶层。
其次,从美国平民阶层的视角看
美国其实是一个精英主义(elitism)和平民主义(populism)交替并存的国家。populism国内中文翻译为“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中文语境下是为了跟民族主义相区分,是具有贬义的一个中文词。但在美国,populism其实并非充满贬义,反而有着令人动容的历史。
19世纪末,美国农民协进会(Grange)掀起了格兰其运动(Grange Movement)。当时美国铁路大发展,但铁路运输费用畸高,农产品的收入大部分都归于垄断的铁路巨头。工业化的垄断利益阻碍了美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这时候美国农民起身反抗,在populism的旗号下,掀起了Grange Movement。这个运动的直接结果,是1870年代在中西部四个州颁布了Grange Law,这些州法实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垄断利益的限制,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国家对经济的干预。Grange Movement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实现了乡村间的免邮费服务。正是因为这项免邮服务,商业企业通过向农民免费邮递产品画册,农民再通过画册选购产品这种今天电商模式的前身,才在美国兴起,Richard.W.Sears最初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Sears百货的扩张,成就了美国商业史上的传奇。
Populism与Progressivism(进步主义)的关系也极为紧密。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在历史上对限制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反垄断、消费者保护、劳工权益保障,都是在“进步主义”这个旗号下在美国推开的。如果没有进步主义运动,美国的社会撕裂早就令其无法发展至今了。进步主义是美国民主党的遗产,桑德斯和沃伦此次竞选也是在进步主义的旗号下展开。基于平民利益的运动,通过立法约束,去改变成形的美国国内经济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实现了美国内部利益的重组。我们可以把美国平民主义(左翼)和精英主义(右翼)交替执政,理解成美国解决既得利益与平民利益长期冲突的基本方式。这种交替不是固定或突发的,而是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阶段,才经由一种社会运动去在政治上加以实现。而这种社会运动带来的政治变革,往往会通过立法的方式强制改变美国的经济形态,实现利益格局的调整。
我们看到,今天国内大多数认为美国无法离开中国产业链的观点,都是从“美国企业必然追求利益优先,不可能放着成本更低的中国产业链不顾、有钱不赚”这个视角来得出结论的。这种完全站在中国自身和美国资本立场的观点,恰恰忽视了美国国内巨大的平民力量。而我们今天身处这个时代,恰恰又是美国平民阶层开始通过政治和社会运动向美国精英阶层宣战,要求利益重组的时代。当美国60%的中下层民众身处今日困境时,他们既可能选举出热衷于贸易战的共和党总统,也可能选举出直接切割产业链而强迫工作机会回归的其他总统。有针对的(而非广泛的)关税壁垒举措,一直都是不同国家选择保护国内弱势群体的有利武器。例如日本,因其农业阶层的强势,使得日本农产品关税壁垒一直存在,这让本不强大的日本农业一直在国内处于被工业高价反哺的地位。这个市场一旦可能被彻底打开,日本农业群体就会对政府投下不信任一票。
我们要以历史的视角来关注美国目前平民主义运动的发展,不能简单将其归结为中文语境下的民粹情绪,更不能将其理解为美式义和团。我们要认识到,在美国因其国内困境,必然要放弃本轮全球化的前提下,美国的平民力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仅仅站在美国资本利益的视角去看待未来的中美关系,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过去三十年,美国资本与中国劳动力的配合是极其紧密的,而这种紧密,正是目前美国民众被引导以拒斥的。
二、全球化进入重构期
很显然,全球化不可能因为美国的放弃就归于消亡,这也并非美国的追求。美国基于现实考虑,必然要放弃的,是由其主导的本轮全球化,也就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下形成的WTO体系下的全球化。由于主导国家的后撤,将导致其他国家纷纷发生连锁反应。美国放弃本轮超级全球化,很可能会退回到GATT时期有限的全球化时代。GATT时代的特点,是各国纷纷保留了不同的贸易壁垒(尤其是关税壁垒),用以保护本国弱势产业和群体。
WTO时代的最得益者,应当还是中国。从WTO时代退回到GATT时代,或者类似GATT的时代,应该不会重复经历曾经各国向心凝聚的过程,而会经历一个美国希望与中国脱钩,进而去推动“去中国化”,但相当多数国家无法离开美国和/或中国,进而不停出现双边/多边贸易谈判这一过程。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全球化的格局可能会呈现以下变化:
1、美国基于其国内再平衡的需要,基于平民力量推动相关立法,将与中国逐渐疏离,进而重建其国内的社会保障网络,同时持续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
2、中美两国分别会寻求与其他国家达成双边或多边协定,以维持足够的全球贸易规模。美国将继续施压于其他国家,以实现与其他国家集体“去中国化”的目标;而中国必须在接受与美国逐渐疏离的现实后,有效的抑制其他国家参与到美国集体“去中国化”的目标中去。
3、其他国家将在上述美国的拉拢与中国的反制过程中,细致考虑处理与中美的关系,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这两个市场,都是它们不可或缺的;但中美之间的较量,又为他们提供了要价的机会。
总体而言,中美的疏离,并不会瓦解整个全球化格局。欧洲和东亚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网络仍然有效,尽管这损失了经济的活力,但正如人类在疫情面前所呈现的,和平时期最令人珍贵的恐怕不是追求财富的极度繁荣,而是大多数人期盼获得的现代文明下的人类尊严。欧洲的不统一,和东亚其他国家的小规模,使它们无法选择跟随极端的孤立主义。欧洲和日本的社会保障网络,事实上成为了这次全球化剧变浪潮中的重要砥柱。
以上是我们对全球化目前和未来一个阶段的基本认识,我们将目前这个阶段称为“全球化的重构期”。这个重构期并没有瓦解全球化,但全球化的格局和规则的确正在重写。重构期仍然会有诸多较量,总体而言,大多数国家都要承受变动带来的阻力。
全球产业链将跟随主导国家的变化而开始重组。美国不可能将全部产业链外迁,但在前述背景下,有可能做到“能迁尽迁”,高度依赖这一产业链的中国企业应当做好万全准备。涉欧洲和日本的产业链不会简单跟随美国外迁,它们很大程度上是要做出自己的成本评估,中国在此的挑战是如何有效降低成本,维持供需稳定。应当比较有信心的是,欧洲和东亚的主要外向型经济体,都无法离开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
中国还应当从美国今天的境况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加大教育、医疗等关键必需公共资源的投入,是极其重要的,这方面应当向欧洲和东亚的先进国家学习,而不是向美国学习。进一步降低制造业成本,将不分高低贵贱的强大生产能力尽可能的长期保留在本国,而不是眼见其流向他乡,是必须有所为的选择。不要寄希望于依赖少数几个行业和少数几个企业去解决14亿人的就业问题,也不要把眼睛盯在美国证券市场中概股估值的幻象上,美国金融自由化的恶果,应当时时加以自醒。
新冠疫情对全球化提出了更现实的挑战。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美国基于疏离中国的决策,将会继续借疫情污名化中国,以拉拢他国实现“集体去中国化”。没有任何必要将民主党打击Trump的言论,视为对中国的支持,这仅仅是美国国内的党争。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一致对外才是两党目前的选择。此时头脑应当更为警醒,更应当站在全球的视角,站在不同国家内部的视角去看待问题。应当充分了解并且理解各国所面临的现实处境,无论是疫情现实还是经济现实。这个阶段与其去宣传自己的认识,不如主动去了解和倾听,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对外推心置腹的本事和经验,不妨时时温习。
身处这个全球化变革的大时代,中国能为、应为的事还非常多。即便目前中美疏离,也不代表将老死不相往来。年轻一代,应当尽早跳出无意义的国内纷争,将眼光放得更为长远。我们不妨思考,当西、葡、荷离开世界中央时,英国人做了什么;当英国人离开世界中央时,美国人做了什么。未来的中国是否会在世界的中央,还是跌入另一个现代化陷阱,全在你们的选择。
以上来源:慕峰
2020年0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