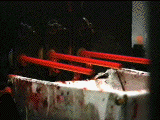"基谱"记录人在一根绳子上组合两种颜色,从而使颜色编码非常细腻,如此,他就保留了两种颜色的意义,而不是让这根绳子负载新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一根单色的绳子中的某一段,与另一根纱线搓成条,或者与另一根纱线搓成斑驳的颜色。于是,整根绳子是一种意义,插入的一段是另一种意义。
在大多数情况下,绳子上都打了若干结,结扣代表数量的多少。而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在给绳子打结之前,先要准备完整的、无结的"基谱"。首先要完成"基谱"的总体设计和构造,包括绳子的连接类型、相对位置、颜色的挑选,甚至包括具有个性色彩的最后的装饰。在有些情况下,"基谱"和其他绳子构成一个组合。一些组合里包含着不同加工阶段的"基谱",既有初级加工的"基谱",也有业已完成尚未打结的空白"基谱",还有带有一些或所有结扣的、完全加工好了的"基谱"。凡是游离于"基谱"之外的有结扣的绳子,显然是"基谱"损坏以后脱落下来的绳子。
"基谱"记录人需要什么特殊才能呢?他在印加帝国官僚体制里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呢?一位"基谱"记录人以什么方式区别于其他的记录人呢?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呢?这些问题饶有趣味,都是需要予以解答的。通向答案的道路,常常就像匮乏的信息所构成的细小或不实的线索,而且其间还有许多断裂的鸿沟,例如,外来文化的引进就形成虚线里的空白。最后,即便回答了所有问题之后,呈现给我们的"基谱"记录人的图像仍然是云遮雾罩、晦暗不清的。
记录者所用的材料通常是染色的纱线,有时也会用毛线,这使我们对其能力有所了解。如果将记录者使用的材料与其他文明里的类似记录者所用材料做一番比较,他们的能力就显而易见了。
在人类历史上,许多材料曾被用来记录信息。石头、兽皮、黏土、丝绸,还有植物的不同部分——比如树干、树皮、树叶和树浆等,都曾用于记事。在某种文明中,用作媒介的材料常常在这种文明所处的环境中随处可见。(一个地区同时使用多种媒介是晚近出现的现象。即使只用两种媒介,总有一种媒介占主导地位,并终将取代另一种媒介。)每一种媒介都有一系列特别的性能。为了和"基谱"记录者所使用的纱线和毛线相比较,我们挑选苏美尔书写人所用的泥板和埃及记录者所用的莎草纸来进行详细的分析。
苏美尔抄写员生活在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年代约为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1700年之间。他们所采用的粘土取自河岸。人们将黏土捏制成不同尺寸的泥版——小的像邮票那么大,大的则有枕头的大小。(由于功能各异,黏土被做成平板、棱柱或圆筒形。)书写人在泥板上画出一条条横跨整个泥版的横线,然后把字符写在这些横线上。这样就完成了记录前的准备工作。他们用的书写工具是苇管做的硬笔——它大约有一根短铅笔那样的长度,硬笔一端被削尖,以便在柔软湿润的泥板上能刻出楔形的划痕。如果抄写员所生活的年代是在楔形文字流行的1000多年中的前半期,那么他们按纵向方向进行刻写,也就是按照自上而上的方向抄写。
后来,他们从左到右地横向抄写。泥版的一面写满之后,书写人将其上下颠倒,翻过来在背面书写。书写必须要快,因为黏土干得快,会很快变得坚硬而难以刻写;一旦泥版硬结,抹掉、添加等任何修改也都不再可能。一块泥板不够书写,或者抄写员还没来得及写完泥版就干了的话,他就开始用第二块继续抄写。书写完毕以后,他将泥版置于阳光下曝晒,或在炉窑中焙烧,以便使他书写的文字永久定型……
大约在同样的年代里,埃及的抄书人使用的媒介是莎草纸。莎草纸取材于高大的纸莎草的茎干;这种草生长在沼泽低洼地,十分繁茂。刚刚割下来的纸莎草的茎干被切成段,去掉外皮,里面柔软的茎肉被平铺展开,捶打,直至成纸张。杆芯里面的天然树胶是黏合剂。一张莎草纸大约6英寸宽、9英寸长,呈白色或浅色,表面闪亮、光滑,而且纸张有韧性。晾干的莎草纸可以用胶黏合连成卷,例如,20张纸可以黏结成6英尺长的条幅。埃及抄书人用软笔和墨水书写。做软笔时,他们切取一截长1英尺的灯芯草,将一头削尖,击打以分离其纤维。他的墨水实际上是一些小饼,像现代的水彩颜料,其用法也与水彩相当。黑墨是用烟灰制成的,红墨原料则来自赭石。埃及的抄写员在书写时能轻快地从莎草纸的右侧移向左侧。
"基谱"记录人和苏美尔及埃及书写人的明显差别是,"基谱"记录人不用书写工具。做记录时,他们用手指头在"基谱"的空间里操作,比如在打结的过程中,他将一条绳子变成了包含大量信息的记录。一切操作都不是预备步骤,整个过程都是记录的过程。相反,苏美尔人需要手握硬笔,埃及人则拿着软笔,书写要经过学习才能会,而且学习的内容包括对触感的培训。"基谱"记录人的记录方式是一种直接构造的方式,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敏感的触觉。
实际上,"基谱"的总体美和触觉相联;记录的方式和记录本身都富有很强的节奏感——前者是有节律的行为,后者产生了韵律分明的成果。我们很少意识到触觉的潜力,而且通常意识不到触觉和节奏的关系。然而,凡是熟悉抚摸的人,对触觉和节奏之间的联系都能够立即心领神会。实际上,触觉的敏感始于胎儿感觉到的环境的脉动,触觉早在其他感觉发展之前就得以开发了。
颜色是另一种明显的反差:苏美尔人不用颜色,埃及人用两种颜色(黑色和红色),印加人用数以百计的颜色。三种记录方式都需要敏锐的视力;但唯有"基谱"记录人不得不识别并牢记颜色差异,以便有效地加以利用。他们的颜色"词汇量"很大,不是简单的红色、绿色、白色等,而是各种红色、各种绿色、各种白色。面对这个庞大的颜色库,他的任务是挑选、组合和安排各种颜色,从而通过不同的模式,表达他所记录的任何事项。
面对"基谱"时,很难立即理解其所表达的含义,因为毕竟各种颜色的运用过于复杂了。"基谱"记录人及其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人之所以能理解复杂的颜色,那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能够看到各种颜色的纺织品——这是他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这就像是我们能够理解复调音乐,是由于我们经常听到这类音乐。一位绘画史专家可以通过音乐意象理解画作,而我们的文化中的另一些人,也可能将对安第斯山区的彩色构图的理解翻译为音乐篇章。在他们的音乐意象的底层,潜隐着一种形式化的模式和结构,而它们还可能被翻译成数学语言。
第三种差异大概是最重要的差异。苏美尔人和埃及人都在平面上记录。在这方面,莎草纸优于泥版。比如,莎草纸可以增长或剪短,其尺寸由此而改变;而泥版一旦做成,其尺寸大小就无法改变了。"基谱"和莎草纸及泥版截然不同,"基谱"的绳子完全不构成任何平面。莎草纸或泥版上的书写,多多少少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抄写的方向或从上到下,或从右到左,或从左到右。这是一种线性的构图。与此相反,"基谱"的记录则是非线性的,这样的非线性,是所用材料产生的结果。
一组绳子占有的空间没有特定的方向;在"基谱"记录员将绳子相互编织在一起的过程中,"基谱"的空间就由绳子打结的位置决定了。这些节点的确定,不必遵守固定的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的序列。绳子的相对位置由节点的位置决定;而且正是绳子的相对位置连同其颜色和上面的结点,决定着"基谱"所记录的含义。由此可见,其基本原理是,"基谱"记录人必须有能力用颜色在三维空间中,构想并实施他要记录的意义。
基谱"记录人可以恰如其分地被安置在印加王国所发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中的某个位置,但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位置?从理论上说,他应该拥有享受特权的地位。那么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的确有一个强有力的佐证,支持着我们理论上的设想。
印加王国拥有庞大的机构、常备军,以及作为国家应有的其他特征,并且在那里存在着一个官僚体制,管理着国家的各项事务。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官僚行政管理"……根本上说是在知识的基础上实行控制"。在此,所需要的知识都被记录下来了。这些记录加上行驶"官方职能"的人们,构成负责国家事务的"政府机构"。管理机构记录一切可以记录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可以量化的事情:例如,居住在某地的居民人数、某村纳税的情况、河水上涨的日子。官僚体制相信自己管理行为的合理性,而这些记录也令执政者心安理得。记录越多,官僚体制处理事务的经验就越丰富,对国家的控制权就越大。官僚体制的记录本身就是这个科层体系的专有财产,而且官僚们竭尽全力保持着记录的这种特性。
在印加王国里,"基谱"记录人为官僚体制做记录。比如,他知道,一组村落里有多少男子适合服兵役,多少人可以派去采矿,他还知道其他很多有趣的事情。他的工作就是处理特殊的、秘密的信息,所以他享有特权。我们认为,他应该是比普通人更为重要的;不过,他的地位不如真正重要的人,后者要么是对其所生活的社区拥有统治权的人,要么是监督、管理着普通印加人的人。来源:互联网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