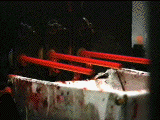.jpg)

热点排行
一支画笔,一支钢笔,为艺术家们画像
【热点观察】
一支画笔,一支钢笔,为艺术家们画像
——与冯骥才对谈新作《艺术家们》
光明日报记者 韩寒
在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几位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生活悄然起步。纯粹的艺术激情引领着他们御风前行。面对社会风雨,深陷生活漩涡,他们该怎样支撑理想,又何以经营各自的艺术与人生?日前,著名作家、画家、文化学者冯骥才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品以几位青年艺术家的人生经历为轴,向人们展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艺术家群体的生活故事和创作历程,是一代人的“生命史、心灵史、艺术追求史”。
绘画、音乐等领域的艺术家是国内文学作品中较少聚焦的群体,而集作家、画家、文化学者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冯骥才,有着书写这个群体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近日,记者与冯骥才围绕《艺术家们》进行了一场笔谈,听他讲述对于个人与时代关系的思考以及对绘画、文学、音乐等多种艺术门类的体悟。
“艺术家热爱的应该是自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艺术中的自己”
记者:《艺术家们》是一部讲述艺术家群体在时代大潮中探索自己精神世界和人生道路的故事。您认为,艺术家与时代是怎样的关系?
冯骥才:一直以来,我都想用“两支笔”来写一部小说,一支是钢笔,一支是画笔。我想用钢笔来写一群画家的非凡追求与迥然不同的命运,用画笔来写唯画家们才具有的感知。在《艺术家们》中,我着重写了楚云天、洛夫、罗潜三位主人公。“文革”时期,他们因对艺术的共同爱好而成为挚友。改革开放后,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楚云天对艺术的纯粹性多有坚守;洛夫随波逐流,最终被市场裹挟,导致悲剧发生;罗潜一直走不出一己的世界,疏离于社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除各自精神性格不同外,小说还写了社会现实因素对他们的影响。
艺术家与时代关系的问题一直在讨论。在我看来,艺术家在社会上是一个群体,而在艺术创作中却是一个个纯粹的个体。他们身处社会生活的洪流中,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与艺术成就都不同。每个艺术家都心怀理想,渴望成就一番事业。为什么有的艺术家会沉沦下去,而有的始终砥砺前行?关键原因有两点:一是能否坚守初心,永远恪守自己的艺术理想,心无旁骛,甘于寂寞,不被任何世俗的功利所诱惑;二是能否始终积极面对生活,勇于站在时代前沿追求更美好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家是社会生活的奉献者而非索取者,热爱的应该是自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艺术中的自己。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家还要洁身自好。
记者:作家艺术家应该怎样表现和书写时代?
冯骥才: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真正的艺术都是富于激情的。艺术家只有勇立时代潮头,潜入生活深处,才能找到生活真谛,获得艺术激情。以我个人为例,我现在作画,与数十年前作为一个纯画家作画不同。以前我是站在纯画家的立场上作画,现在我是从写作人的立场出发来作画。尽管现在我也从作画中追求纯艺术的愉悦,但我不是为自娱而画,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袤的现实。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人的思想观念是复杂的,庸俗的价值观会腐蚀人的心灵。艺术家作为精神事业的工作者,其工作的本质是用“真、善、美”帮助人们抵制“假、恶、丑”,从而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对作家艺术家而言,价值观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以纯正的价值观去观察生活、判断生活,作品才能更具思想价值,才能深刻地表现生活,积极地影响生活。
“我往往从艺术的角度来欣赏文学”
记者:语言是活化一部小说的灵魂,《艺术家们》里就有不少妙语,如“荒原上的野花是美丽的天意”“风是天上的罗丹,天天雕刻着天上的云彩”。在您看来,怎样活化一部小说的语言?
冯骥才:这也是一个很个人化的问题,我只能谈谈我的情况。在从事文学工作之前,我的专业一直是绘画。进入文坛后,绘画一度中断。我天生热爱艺术,绘画、音乐、诗歌、民间艺术等对我都有无穷的吸引力,也让我往往从艺术的角度来欣赏文学。这使我产生了写《艺术家们》这样一部小说的冲动。
不过,这里边有一个与我们文化传统相关的问题值得探讨,就是中国人所讲求的“琴棋书画”和“触类旁通”。在过去,一个好的画家必然有很深的诗文修养。唯有如此,他们笔下的层峦叠嶂、林海丛莽、仕女高士、草木生灵才会具有灵魂。技艺只是浅层问题,背后更深的其实是哲学、文学、文化和美学问题。这个传统有助于全面提升人的修养和审美能力,也是中华文化的高明之处,今天应该将其融入教育体系和对青少年的培养中。
记者:您曾表示契诃夫有一颗悲悯之心,而您受契诃夫的影响较大,在《艺术家们》中,您是怎样体现作家的悲悯之心的?
冯骥才:悲悯是一种人性关怀,是感同身受的情感,是对处在困境中的弱者的同情,常常能唤醒世间的正义、公平与爱心。作家艺术家尤其应具有悲悯的情怀。契诃夫有悲悯情怀并因此伟大。鲁迅也有这种情怀,这在《伤逝》里表现得十分充分和感人。
在《艺术家们》中,我尽量让主人公心中富有这种“柔软的力量”。例如,楚云天善解人意,从不强加于人。他卖了几幅自己的得意之作,默默买下好友洛夫将要拍卖而不应卖掉的代表作,打算将来有一天再送还给他。
我给不同人物安排了不同的命运,不回避写作的批判性,同时我也给全篇定下了理想主义、唯美主义的基调,因为我相信追求美和善是发自人心灵的自觉。我的读者一半是我的同代人,一半比我年轻。对于书中的故事,我的同代人一定感同身受。至于比我年轻的读者,我更希望他们通过读懂书中人物的幸与不幸,与艺术家们成为知己。
“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无与伦比的美学系统”
记者:您在《艺术家们》中写到了中国艺术家走出国门的故事,这就会触碰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关系的问题。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传统的文化艺术?
冯骥才:我认为,在总结、认识和研究传统艺术与舶来艺术方面,一直是两张皮,中间缺少融合点。我们没有把创造性发展自己的艺术作为主体,结果误以为“传统落后于时代”,因而漠视传统,甚至妄自菲薄。《艺术家们》中有一处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谈话值得一提。楚云天赴维也纳现代艺术博物馆看奥地利已故作家马克斯·魏勒的画。策展人告诉他,马克斯·魏勒不关心具象,他从中国古代绘画中汲取到的是一种从容、大气、豪迈、灵动以及对大自然的无上崇敬,而西方的风景画没有这种东西。马克斯·魏勒用自己抽象的“形”融汇了中国人的“神”。由此观之,我们的经典艺术形态也可以给外国艺术家启示,关键是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把自己的传统文化放在什么位置。
应该说,当今画坛有一些艺术家致力于为中国艺术的当代化发展而努力,但力量还比较单薄,尚未形成气候。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无与伦比的美学系统,但如何真正让我们的艺术家对自己的美学传统引以为豪,非常值得讨论,尤其是在高校。
记者:您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方面耗费了很多心力。为什么要用近30年的时间,整理木版年画、剪纸、唐卡档案以及口头文学遗产?
冯骥才:这些工作是必须做的,所以我曾放下笔,用很长一段时间来做这个事情。在近30年里,我们的社会急速发展变化,这是历史上从未碰到过的。在这个转型期,农耕文明被现代工业文明渐渐取代。可根植于农耕文明的传统文化中,有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它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基。所以,传统文化遗产中优秀的内容必须传承。
对于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很关键也很紧迫,今天我们保护下来多少,后人就拥有多少。这件事比我个人的创作要重要得多,所以我今天仍旧在做,我会认真做好每一件该做的事。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13日 13版)
2021年0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