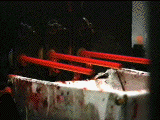.jpg)

热点排行
父亲的字
也许因为太亲近的缘故,我从来没有认认真真端详过父亲的字。
记得在读初中时,我生了一场大病。痊愈后的一天晚上,父亲叫我早点睡,明天去上学,他却铺纸磨墨,用毛笔为我写了一张大大的请假单。台灯下,父亲凝神“舞文弄墨”情景,印在了我的记忆库中。
翌日早晨,我在学校的办公室里把请假单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打开仔细看着,似乎有点惊讶,他又把请假单递给其他几位老师浏览。我感到忐忑不安,不知道父亲写的请假单有什么不妥之处。终于,班主任拍了拍我的头:“上课去吧——你父亲的字很好。”
放学回家后,父亲问我:“老师看了请假单,说了什么吗?”我摇了摇头——我把老师的赞语“贪污”了,因为我不习惯当着父亲的面说这些好话。父亲似乎有点失望。
从这次以后,我才明确地意识到:父亲的字写得很好,不然,老师怎么会赞扬呢?
父亲早年失去双亲,在少年时代来上海当学徒。虽然寄人篱下,他却刻苦勤奋。父亲正是凭借着铁钩银划的一手好字和既快又准的算盘功夫,成了一家大旅社里收入颇丰的“账房先生”。他一直告诫我们:“字就是人的一张脸,字写不好会让人看不起的。”这是他那个时代的箴言。尽管时代已经变迁,毛笔早已被钢笔和圆珠笔取代了,但他依然对毛笔忠贞不二,即使偶尔用钢笔或圆珠笔,他的执笔姿势还是像握着毛笔,而且每个字都有着毛笔字的意韵。父亲的字在我们那条街上很有名,经常有人请他搦管挥毫,他则来者不拒,不仅不收润笔费,还要倒贴笔墨纸张。
平时,父亲写毛笔字时,总叫我为他磨墨,他一定是想让我受些熏陶。可惜我对书法不感兴趣,尤其讨厌临摹字帖,弄得父亲很无奈,后来就不叫我磨墨了。
经过了“文化命大革”的运动,父亲对书法兴味索然,已经懒得再动笔墨。然而在1974年,父亲出人意外地专门到文具店买了几支毛笔。母亲悄悄地告诉我:“你父亲又在磨墨练字了。”一天,父亲突然叫我陪他走走。父子俩走到离家不远的东门路,父亲忽然抬头笑眯眯地问我:“你看,‘德兴馆’几个字写得还可以吗?”我这才发现,这家百年老店的招牌上的大字出于父亲的手笔。平心而论,大概由于搁笔多年的缘故,这几个字远远没有展现父亲“全盛时”的水平,但我还是连声称赞。父亲那天容光焕发,显得特别高兴。从此以后,父亲有事无事总爱到东门路走走。直到3年后,另有人为“德兴馆”重写了招牌,父亲才不再经常逛东门路了……
父亲退休后有点寂寞。在他刚过了80岁生日的一天午后,他躺在沙发上小憩,竟无声无息地永远离开了我们。下午,我闻讯赶到父亲身边,在哭泣中,用父亲留下的毛笔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奠”字……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潘志豪
2006年06月07日